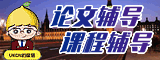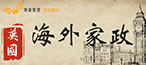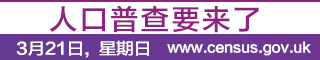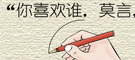性侵我女儿的丈夫死后,我割掉了他的命根子
死者生前极度威风,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号。现在他躺在解剖台上,连个男人都算不上,他的下体血肉模糊,只留下一个茶杯大小的血洞。
这个男人的威风被烧成了灰,阴间里他还可以横行吗?
今天法医陆锐给大家讲一个即痛心又解气的案例——一个女人把她的男人给废了。
2018年2月18日晚上10点,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案,马蹄山下发现了一具女尸。
那时我正被抽调到局协助侦破一件杀人案件,犯罪嫌疑人畏罪潜逃没有半点音讯,案情分析会议上,全局上下正为这个案件焦头烂额。
“又是一起命案?见鬼了!”侦查科刘科长猛地站了起来,两道眉毛拧成了一道线,半截烟蒂被他狠狠地按在烟灰缸里。
这几天他的压力最大,杀人案件案情明明接近明朗,却苦于嫌疑人潜逃而无法收尾。
马蹄山地处四崖村东侧300米,海拔大约500米,山上松木茂密,平日里村民极少上去。
当我们赶到现场,报警的村民正站在那里瑟瑟发抖。
我们顺着他的手指走近尸体,尸体趴在路边的水沟里,一只手还伸向路面。
“不会是冻死的吧,这大冷的天。”按照惯例,我们首先要要确定“死者”是否还有生命体征,如果断定是真正死亡,才会做体表检查。
打开勘测灯,雪白的亮光下死者满身血迹,一件陈旧的紫色碎花棉衣有几处破洞,露出黑色的棉絮。
我把手指伸向尸体的鼻孔,心里一颤,禁不住松了一口气,这个人没有死,只是处于高度昏迷状态。
“人没死,快叫救护车。”我一边对刘科长说,一边在“死者”身上搜查能够证明她身份的东西,令人失望的是,口袋里只有一部耗完电的手机,别的什么也没有。
奇怪的是她身上的血迹,几乎被土尘淹没,看样子已经受伤多日,她是怎么受伤的?伤在哪里?如此寒冷的夜里她为什么出现在这里?
就在这时,救护车呼啸而至,救护人员把伤者抬上车。
看着车辆疾驰而去,我心里忽地闪过一个念头。
一个电话惊醒了四崖村村主任李大海,当他走出村头,等他的警车已经停在那里。
在医院的病房里,我们见到了依然昏迷不醒的伤者,护士已为她换上了病号衣服,擦净了脸庞,李大海看着看着就流了泪。
“就是她,李友凤,我就知道她走不远,她只是一时糊涂。”李大海看着我们,极力为这个杀人犯辩解着。
医生告诉我们,李友凤是因为劳累、饥饿、寒冷所致暂时休克,身体并没有伤痕,很快就会恢复。
李友凤迅速被警方监视治疗,换下来的血衣也被警方带走,身上没有伤痕却浑身血迹,在我心里也已经有了答案,如果这些血迹的DNA鉴定结果对比成功,李友凤难逃法律的制裁。
走出医院,已是凌晨3点,几日的劳累总算有了结果,可是我心中丝毫没有案件破获的快感。
“再软弱的女人也有被逼疯的时候。”刘科长给这个女人的行为总结了答案。
案件的开始要回到过去的3天。
2018年2月15日上午10点,平湖镇派出所值班室走进来一个小女孩,陪同她来的还有一位50多岁的男人。
女孩名叫小翠,家住四崖村,中年男人是村主任李大海。
小女孩一张小脸蒙着一层灰尘,穿着一身校服,衣服又脏又不合体,几乎罩到了屁股。
他们是来报警的,李大海说,小翠看着个子不矮,其实脑子不好使,是个弱智女孩,这几天她总是到村头去望,一看就是半天,好心的村民把小翠带回家里,也没发现她父母的身影,并且,他们在院子里发现了血迹,这才想起来,小翠的父母有几天没露面了,于是这才赶紧来报警。
“有血迹?两个大人能到哪里去?村里没和他们联系吗?”值班民警给李大海倒了杯水。
“电话都关机了,联系不上,小翠的母亲平时连个大门都很少出,几天不回家很不正常,还有,你看……”
李大海把小翠拉倒跟前,用手指了指小翠的裤裆:“小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?怎么会流出了这么多血?”
民警这才着了急,马上安排人把小翠带到了附近的镇医院做了妇科检查,得出的结果很让人痛心,小翠确实是被性侵了,在她的内裤上,还留下了精液的斑痕。
弱智女孩被性侵,就是性质恶劣的刑事案件,况且,小翠仅仅14岁,还是未成年女孩。
派出所民警不敢马虎,立即去了四崖村的小翠家,在院子里靠南墙的一堆木柴下,找到了一具男性尸体,死者就是小翠的父亲刘安成。
中午12点,县局接到派出所电话去了现场,发现死者全身被砍了十几刀。
县局技术科的老刘因病住院,两个实习生手足无措,市局在下午1点接到求助电话后,2点不到,我和痕检员罗林就赶到了现场。
案发现场已被警戒带隔离,围观的村民看到我们来了自动闪出一道缝隙。
院子里破烂不堪,靠南墙是两棵高大的白杨树,树下是一层厚厚的白杨树枯叶,一堆用来烧火的枯枝已被扒开,露出了一具满身血迹的尸体。
死者上身穿一身破旧的秋衣,下身赤裸,颅骨几乎被刀砍成两半,脑浆和血液混合在一起,粘满了死者的头发和脖颈,我打开勘测箱取出剪刀,把被血迹紧紧粘贴在肌肤上的衣服剪开。
根据死者背部尸僵颜色,可以判断死亡时间大约2天前。
死者的胸部被砍了数十刀,刀口深浅不一,几乎没有一刀可以致命,并且伤口生活反应极弱,这种刀伤通常是凶手在死者死后的泄恨行为,颅骨的砍伤才是死者的致命伤。
更让我震惊的是,死者刘安成下体被割,整个生殖器和睾丸没了踪影,被割处留下了一个茶杯大小的血洞。
并且生殖器被切刀口的生活反应也是很弱,看来生殖器是死者死后才被切除。
凶手对死者到底有多大的恨才会做出这样残忍的手段?
凶手显然并没有刻意伪造现场,只是做了简单的藏尸处理,从尸体到房间的方向,还留下了拖拉尸体的痕迹,院子里留下了一道血痕,被尘土遮盖了一部分。
案发第一现场显然是在房内,我和罗林直接走了进去,房间分内外两间,外面是一个砖块砌成的灶台,灶台上是一口大锅,大锅盖子开着,里面是半锅没吃完的稀饭。
“这几天小翠就是靠这一大锅稀饭活着。”村长李大海说,“死者刘安成和妻子李友凤是二婚,女孩小翠是李友凤带过来的,是个弱智女孩,14岁了也没上学,一般也不出门。”
房子的内间是卧室,靠北侧是北方人特有的一座土炕,南侧被一条脏兮兮的布帘隔开,里面摆着一张窄小的木床,上面是一床露出棉絮的被子和几件女孩衣服。
“一家人都睡在一个房间里吗?”我边想边看,伸手在床前拿起一双沾满泥土的蓝色军用鞋子。
穿这双鞋子的应该是一双成年男人的脚,这个男人是谁?小女孩曾被性侵,会不会就是这个男人干的?
我在鞋子内侧提取了检材放到了物证袋里,心里期盼着这双鞋子放到女孩的床下只是一个偶然。
就在这时,罗林也有了发现,在外间的那张大床上,掀开几件衣服,发现了大量的血迹。
枕头上沾满了脑浆和血液,经过搜查,在床头和墙壁的夹缝里,发现了凶手的作案工具:一把沾满血迹的砍刀,刀柄留下了清晰的带血的指纹。
凶手作案已经逃离,现场也没有做任何伪装,所有的证据都说明:在这个破旧的家里,曾在一夜间发生了令人胆寒的杀人事件。
被性侵的女孩,失踪的女人,倒在血泊里被割去生殖器的男人,他们之间曾上演了一连串的悲剧故事,而这些故事的结局最终以这样的一个血腥场面收场。
很快,痕检员罗林在一把木梳上提取到了和刀柄上相同的指纹,死者的妻子成为最大嫌疑人。
况且,从她给弱智女儿留下的最后一大锅稀饭可以看出,她的失踪并不是莫名其妙,很有可能是畏罪潜逃。
那么,死者的妻子到底去了哪里?把弱智女儿独自留在家里她放心吗?她的女儿能不能自己把饭送到嘴里?吃完了这些下一顿饭又在哪里?
她应该还会回来。
现场勘测完成,几个民警把尸体放到裹尸袋抬上了车,围观的村民窃窃私语,有一位老人用拐棍指着尸体在地上吐了口唾沫。
县局侦查科刘科长简单地向我介绍了死者的背景:“死者在村里名声很臭,有个外号叫瘸狗,很多村民说这都是报应。”
死者刘安成,46岁,左脚有残疾,不能干重体力活,在镇上摆了个肉摊。
1998年,因为和同行发生争执把人捅成重伤入狱两年,2002年和离异的邻村女人李友凤结婚。
提起刘安成和李友凤的婚事,村民们忍不住为李友凤叹息:“这都是她的命,她老家是云南,嫁到这里后因为生了个傻女儿丈夫和她离了婚,没想到又嫁给了刘安成这个畜牲。”
李友凤比刘安成小8岁,又稍有姿色,开始夫妻二人倒也和睦。
刘安成继续在镇上卖肉,可是因为他坐过牢名声太臭,生意冷清,不久就撤了摊位。
失去经济来源的刘安成脾气变得暴躁,无所事事的他很快就学会了酗酒,赌博。
结婚第一年,李友凤怀孕了,可是不到2个月就流了产,李友凤曾经说:“刘安成就是个畜生,一夜也不肯放过自己。”
刘安成对李友凤的家暴始于李友凤的第二次坠胎,孩子已经5个月了,李友凤因为刘安成的酗酒发生争执,被醉酒的刘安成推倒在地流了产。
更主要的是,这次流产伤了李友凤的子宫,从那以后一直就没怀上孩子。
从那后,刘安成对李友凤的家暴简直成了习惯。
“经常在夜里听到李友凤的惨叫声,半个村的人都能听到。”李友凤的邻居说,“开始还有人过去劝说,都被刘安成骂了出来。”
李友凤也不是没想过离婚,村主任李大海说:“她曾找过我两次,都被我劝了回去,现在想想,我也是做了孽事。”
李友凤的女儿小翠今年14岁,家里又穷,从来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,现在穿的还是别家孩子穿下来的校服。
“这丫头经常到学校周围转,只有穿上校服,才会学着学生的样子,安静地坐在家里的桌边,还找本书放在桌上。”
对于刘安成的死,村民们也认为是李友凤干的。
“李友凤能在这个家里呆了这么多年,不是一般的忍耐力,这一点比很多女人都厉害。”
也有人提出疑问:“李友凤把男人杀了还是出乎意料,这不是自寻死路吗?还不如铁了心离婚。”
还有人为李友凤鼓掌:“干的好,还把男人的脏东西割了下来,要是换做我我可做不到。”
解剖室里,死者刘安成躺在冰冷的解剖台上,我数了一下,从颅骨到下肢,死者被砍16刀。
除了颅骨伤有着明显的生活反映,其它伤口都是死后或者濒死期所伤。
而颅骨的那一刀用力极狠,几乎把脑袋劈成两半,根本就没有给死者留下还手的余地。
剖开死者的胸腔,腹腔,从肠道内容物的形态可以判断,死者是在饭后5小时左右遇害,也就是2月8日晚上12点左右。
而此时从死者身上和案发现场提取的检材检测结果也出来了,通过对比,小翠裤子上留下的精斑来自她的继父刘安成。
晚上例行的案件分析会议上,县局侦查科刘科长介绍了案件调查情况。
在这个案件里,死者的妻子李友凤是最大嫌疑人,县局已联系交通部门,对车站最近几天的出行人员进行排查,都没有发现李友凤的影子。
“李友凤家很穷,这个女人平时不好说话,被丈夫打了也很少吭声,身无分文的她走不远。”
村长李大海自案发后就把弱智女孩小翠带到了家里,小翠洗了澡,换了一身合体的衣服,如果不注意她脸上的傻笑,14岁的她看起来其实是个蛮漂亮的女孩。
“如果她被抓会不会判死刑?”李大海看着坐在旁边还在傻笑的小翠说出了自己的担忧,“小翠怎么办?我能养她几天,总不能养她一辈子。”
会议上刘科长说:“李友凤回来的可能性很大,不管她是不是凶手,都是侦破案件的关键,警方已安排人员对她的家进行24小时监视。”
可是李友凤就像消失在空气中一样半点没有踪迹,各个沿路遥控也没发现她的踪影,这个身无分文的女人又能去了哪里?
一天,两天……警方对李友凤能够回来的想法感到了怀疑,四崖村三面环山,唯一的外出公路直通县城,15公里处就有了监控摄像头,李友凤没有翅膀,肯定不会飞出去。
还有人大胆设想,李友凤是不是死了,连续的寒冷和饥饿,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。
果然,李友凤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出现了,这才发生了刚开始的那一幕,
2月19日,病房里的李友凤醒了过来,监视她的民警说,醒来后的李友凤焦躁不安,对于医生和护士的询问不说一字。
20日,经过院方的许可,我们在一间单独的病房里见到了她,随同我们来的还有村长李大海和李友凤的女儿小翠。
小翠已经换上了新买的衣服,运动鞋,深蓝色的牛仔裤和粉红色的羽绒棉衣,细心的女民警还为小翠扎了两条辫子,“这一去不知啥时候才能再见到她妈,漂亮一点会让她妈放心。”
病房里,李友凤见到身穿警服的我们显得很慌乱,整个身子直往后缩,当她看到村长李大海和女儿小翠,猛地坐了起来,抱着女儿放声大哭。
“如果不是担心我女儿,我不会回来的。”李友凤稳定了情绪之后,把小翠的手紧紧攥着,眼睛一刻也不肯离开女儿的脸。
说起她杀死丈夫刘安成的经过,李友凤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:“我杀了他,他就是个畜生,我还把他的脏东西剁了下来,扔到炉膛里烧成了灰。”
李友凤眼里放着光,牙齿把嘴唇咬出了深深的血印。
李友凤因为生了弱智女孩小翠被前夫抛弃,嫁给了大她8岁的刘安成:“刘安成年龄比我大,坐过牢名声又不好,我觉得这样的男人可能不会嫌弃我们娘俩,可是结婚不久,我就知道自己想错了。”
李友凤把目光移上窗外,两串眼泪流了下来:“想想那些事情我都浑身发抖,他喝酒,打我,兽性十足,几乎不放过我一个晚上。”
李友凤曾经为刘安成怀过两次身孕,都是因为刘安成酒后施暴流了产。
“第二个孩子没有后,我的子宫再也不能怀孕,那时我很想要个孩子,要不然等我死了,就没有人照顾小翠。”
最近这几年,夫妻生活的不检点让李友凤的妇科疾病越来越重,几乎和刘安成不再过夫妻生活,“我去医院治过几次没有效果,就不想治了,这样也挺好的,只要他不嫌弃我,我就和他把下半辈子混完了。”
2018年2月13日,李友凤和小翠吃过晚饭后就睡了,刘安成照例要喝完那瓶酒。
11点,李友凤被小翠的叫声惊醒的,发现刘安成光着身子趴在小翠身上。
“我知道这个畜牲干了什么,拼命过去撕扯他,被他一把推倒墙角,我当时就晕了过去,等我再次醒了过来,那个畜牲已经睡了,小翠睁着眼躺在那里,床单上都流了血。”
李友凤抱着小翠哭了一会,给她穿好了衣服,看到熟睡的刘安成,起了杀心。
外间房子锅灶旁边就是一把锋利的砍刀,这把刀她用惯了,是专门砍山上的硬木的,她拿了起来,毫不犹豫地对着刘安成的脑袋砍了下去。
“我必须一刀把他砍死,要不然他会杀了我们娘俩。”想起那一幕,李友凤还有余悸,“他像头猪一样哼了一声就没了动静,血液溅了我一身,这个男人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。”
杀人后,李友凤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,可是她知道杀人就要偿命,自己也活不了。
最终她决定逃走:“横竖都是个死,侥幸活了,我还能给小翠挣碗饭吃。”
在决定出逃的时候,她唯恐刘安成不死,拿起砍刀又在尸体上砍了十几下,看到刘安成赤裸的下体,又把他的生殖器砍了下来,放到了炉膛里。
“他下辈子也别想再做个男人。”李友凤眼里露出了少有的凶光。
她为逃走做着最后的准备,她把锅里放上小米,足有2斤,够小翠吃几天了,明天也许丈夫的死就会被发现,村里会给小翠一碗饭吃,他们不会见死不救。
然后她点燃炉灶,不一会就从灶膛里飘出了一股特有的焦香味:“那一刻我感到从没有过的痛快。”
临走的时候,她把尸体拖到院子里用木柴盖住:“我怕小翠看到尸体害怕。”
然后躲在离村300米的马蹄山里,想看一下这几天的情况再说,这座山她熟悉,再往前走穿过另一座山头就是国道,只要她不坐车,不住店,就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
可是没想到2天过后村里还是没有动静,饥饿和寒冷却逐渐在消耗着她的体力,直到第4天,她才看到警车从山下的马路经过,她已经没有力气翻过那座山了。
“我感到我要死了,脑子里只想再见小翠一面,再不下山就来不及了。”李友凤流着泪说,“小翠太命苦,我都不知道以后她的日子怎么过,临死前我还是想叮嘱她几句,也不管她能不能听懂。”
她抬起头来把目光看上了村主任李大海:“我想过和那个畜牲离婚,被你拦住了,现在我不恨你了,都怪我自己没有主见。我有个要求,以后……以后村里能不能给小翠一碗饭吃。”
李大海脸一红:“你死不了,村里的人会出庭为你做证的,孩子的事我都想好了,送到孤儿院吧,那里的条件要比家里好,也更安全,你好好改造,争取早一天出来。”
李友凤点了点头,然后伸出了手,示意我们给她戴上手铐。
临走时,李友凤走到小翠面前蹲下身来用手抚着她的辫子。
小翠全然不懂那是母亲对她的亲昵,只是伸出手摸了摸母亲手上那副铮亮的手铐。
页:
[1]